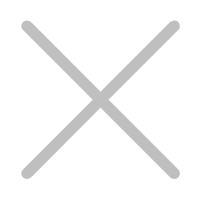第一章 奔放的花骨朵
<1>
多年来,我一直想着阿满.那个小时候邋遢不堪的 *** ,他双手沾满了油渍,来回抹在自己灰白色的土布裤子上,鼻水在鼻子边徘徊,一脸傻笑的看着我.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,我在翻阅这些记忆的瞬间,被几幅画面给触动,渐渐的知道,有些往事,不是脚踏过去,就可以遗忘的,挡在面前的是一扇破旧摇晃的大门,就算不推开门,往事也可以在裂缝中象花儿一样的绽开.
一九七六年的冬天,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.却不料那年冬天村里下起了一场冰雹,石头块大小的冰雹辟厉啪啦的敲击着瓦顶,屋顶在颤抖歌唱.生我的女人在天灰蒙蒙亮开始阵痛,她淌着泥水,跌跌撞撞的捂着大肚子,忍着疼痛,艰难步行到一公里外的接生婆家,说她快死了,生个孩子没拉屎般简单.就这样,我在女人的呐喊声中开始做女人.奶奶后来说起,归根结底,生我的女人是个可怜的女人,她受尽了生活给予的一切磨难.
开始满嘴YY,蹒跚学步,可我还没学会叫爹妈,就再也没见过生我的女人.于是,越长越娇俏,开始记事,在村口,只要张开双眼,丑陋的事物随处可见,满嘴脏话的大汉,衣裳不整的荡妇,包括女人下体的器官.那站着撒尿的女人也绝非善男信女,动作娴熟仿佛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,如同狗一般的机灵与随意.上了年纪的老大爷告诉我,看见这样的女人,可以朝她的屁股狠狠的揣上几脚,知道她一个跟斗摔倒,再让她爬起来,庄重的做女人.
除了哥哥,我儿时还有两个玩得较好的玩伴.一个是我五岁那年在镇上卖鸡蛋认识的同村女娃江小渔,她父亲是外乡的渔民,上门做女婿.江小渔从小就喜欢穿着大红大绿的花布裙在镇上招摇的 *** ,凭着三岁就能背颂老三篇和床前明月光,一度被村里人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天才.奶奶却说这 *** 轻浮,没个村姑样,迟早要回归到最初的样子的.另外一个是长我三岁的邻居阿满.我不知道阿满为什么在后来那么的讨厌我,甚至躲起来不见我,直到我离开村子进了城.
小时候在一块,最喜欢的游戏要属小马过河,加上哥哥,四个人一起玩,两人一组,我和阿满,江小渔和哥哥,从一开始就说好的,不交换玩伴,只要谁过得了地上用瓦砾划分的对方界线,把对方推下河,谁就是赢家.江小渔没有赢过.
那个晚上,江小渔没有回家,她和我睡一个房间.糟糕的小床.零乱的被褥,浓重的霉味,她在密谋,她让我下次再玩小马过河的时候,换个游戏规则,把年纪最大的阿满双眼给蒙上,把他推下河,玩更好玩的游戏.我充满了好奇,想都没想就答应了.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骗人.第二天清晨,阿满乐呵呵象没事似的来找我们玩.象预先预谋好的,我让阿满蒙着眼睛,他一开始出界,我就把他推下了河界.江小渔就这样带走了蒙着眼还懵懂的阿满.还不让我跟着,我一个人泱泱不快的回家了.
我到夜里一直都没睡着,从隔壁传来了阿满妈妈的嚎淘大哭声.隔天,阿满满脸伤痕的捂着下身经过我家门时,张口就骂我是个骗子,玩弄了他,会有报应的.我惊愕不已.我不知道江小渔究竟对阿满做了什么,那以后,江小渔一下子没了音讯.那一年,我仅仅十岁.
没多久,我们全家逃荒似的逃离了村子到城里,上了拖拉机,我忍不住回头望去,隐约看见阿满的眼神,从门框里小心翼翼的望着,与所有那些愤怒的少溺爱眼神一致,带着些少的天真与纯洁.车渐渐远去,把瘦弱的阿满抛在了尘土中,直到我视线模糊.
一家人就暂住在城里老巷子里的一所老平房里.旧房子的门前有条阴沟,不宽,约四十厘米高,一到夏天,恶臭难挡,时常捂着鼻子才能越过.夏天的夜晚,硕大的老鼠就会在阴沟里欢快的乱窜践踏,大概在漆黑里总是会撞得焦头烂额.一家人,实际只有三口,我,哥哥,还有父亲后来娶进门的女人.那女人时常不穿衣服,从旧房子对面分离开来的洗澡房里款款走进屋子,视若无睹,她没亮灯,皎洁月光映射下的女人铜提宛若似水银布,闪闪发亮,她打着赤脚走进自己的屋里,门没掩上,直接躺在双人竹席大床上,望着天花板发呆,有时一呆就是一夜,嘴里偶尔喃喃自语.
那女人带着我们离开旧房子的时候,老巷子里那棵高大的苦楝树已经被白蚁侵蚀得摇摇欲坠,走的时候,女人身上背着黑色的大挎包,有些吃力的走着,牵着我的手,哥哥就跟在后头,我悄悄的回头告诉那棵树,等我再长大些,我会回来替它收拾残骸的.
没钱时,我那个长我两岁的哥哥就会跑到附近施工的工地上捡些废弃的垃圾,破铜烂铁,水泥塑料袋,民工喝光的酒瓶子之类的,拿到国营的收购站里卖,换取零钱.一个酒瓶子一毛八分,哥哥给我买糖吃,红双喜的硬糖,一分钱一颗,一毛钱十颗.卖糖的是个七,八来岁的小姑娘,看上去不美,哥哥故意把钱丢在柜台底下,趁姑娘弯腰时候,我伸手进糖罐子里抓了一把,偷偷塞进口袋里.那是世界上让我吃着可以泪流满面,可以甜到心坎里的糖.有时一日三餐全是馒头,铁路的老面馒头,尽管有的时候已经腻到无味,却也不停的啃,哥哥个头大,吃得多,吃得跨快,时常被噎着.
那女人不吃,躲起来,说不饿,我看见她常常喝水.
工地里的民工大都和我们一样,从村子到城里想讨碗香饭吃的,每每路过工地,那个些眼神猥琐的民工总会盯着我后妈看上个大半天.有时候会嘲讽哥哥是李大傻,说我妈是男人跨下的一块肥肉,花个几元钱,就能摸她的下身,咬上几口.卖那个的.
有一回哥哥被打了.他不敢回家,墨绿色的帆布书包被几个人高马大的民工给抛起扯烂,他双手捧着被人用彩笔画得面目全非的课本,红肿的脸颊低垂着脸.垂头丧气的躲在出租房楼梯口下蹲着.那女人出门了,没回来.
那夜晚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,我不敢入睡,害怕.害怕一闭上眼睛就做梦,做那个时常会出现在脑海里的梦,一片荒凉的玉米地里,一片狼籍,一个饿极了的孕妇活活被晒死在了地里,还有一个婴儿的背影.
那女人回来已是午夜,她身后跟着一个大约四十来岁的男人,男人身材高壮.穿着合体的白色衬衫,黑色的西裤.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,看上去不象是坏人.高大的男子和娇小的女人并排着站在一块,极登对.他们似乎有意隐瞒着自己的年龄和身份.女人自从到了城里,已经学会了擦金抹粉,出门前,她显然化了厚重的妆,可妆有些花了.
对于突然其来出现在狭小客厅里昏昏欲睡的我,他们两人有些不知所措.稍微停顿了一会,男人才开口说话.
"你女儿长得很漂亮"
那是一间仅有三十来平米的旧居民楼,是间俗不可耐的屋子,墙上的粉底斑斑落下,底色上污垢重重,是一副狰狞怪异的图案.杂乱无章的屋子,时刻散发着给人以陈旧与腐烂的感觉.
男人坐在椅子上,看着屋子的陈设,时不时摇晃着脑袋,趁女人下楼的空隙,偷偷将我仔细打量了一番,我不敢看他.
十六岁的我,渴望拥有一部自行车,厌倦步行.时常会想出走多年的村庄,想村里的每一场大雨,想玉米地里散发的清香.想阿满,那个骨瘦如柴的少年.
遇见四十岁男人,我开始想象,想象着在某一天,自己老了,老到牙齿掉光,满脸皱纹,说话含糊,一个人依靠在家乡的老树旁,与它一起终老.一个女人能如此优雅的死去,对与她而言,即使年迈落迫,在人生的最后门槛上,依旧繁花似锦.
未完待续......